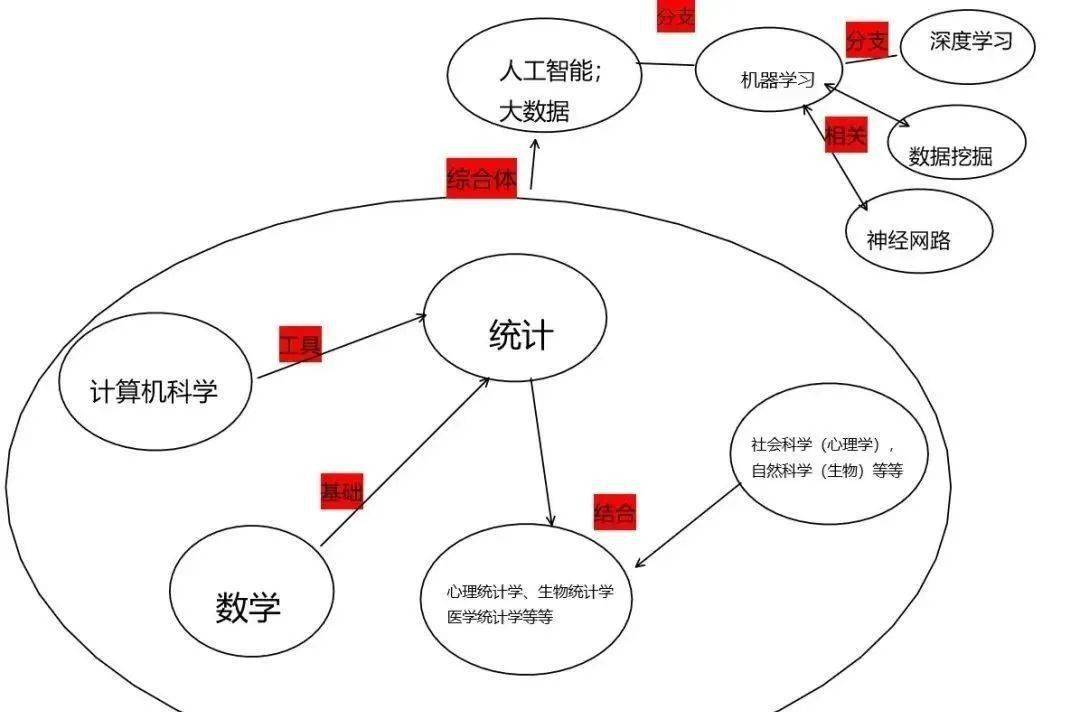在明代中后期,文人面临的生存抉择
文人群体开始关注内心世界,个人意识觉醒,尝试以开放的心态去对待另类的思想和学派,审美意向、政治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观念上都出现了多元共存的倾向。
这里明代中后期兰亭图中所体现的文人矛盾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雅俗之分,一个是仕隐的困惑。

雅俗之辩是从文化观念上来剖析文人雅俗心理的碰撞,从雅俗的互动到文人审美意识的确立,另外从哲学思想上来解读文人的仕隐困惑,从心态的矛盾到行为的抉择。
(1)雅俗之辩
雅与俗的问题究其根本是文化观念的差异,即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但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是属于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且这两种文化相互影响。
明代诗人袁宗道在诗歌阐明了雅文化和俗文化都是来源于自然社会,没有必要完全分清界限,以包容开放的态度看待雅俗,文化艺术创作更加能呈现多样面貌。明代中后期随着市民文化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对文人阶层形成冲击,文人在面对大众文化时所产生的焦虑。

这种焦虑就是雅俗之辩的问题所在,雅俗之别就在于其独特的生活风格与价值体系。
明代中后期文人引领起来的各项活动都在宣扬雅俗标准,还有将大众文化融入到文艺创作中,雅俗之辩主要在两方面,一个是绘画趣味;另一个是生活习惯方面。
绘画的审美趣味是中国山水画的表现核心,一直是以表现主观性灵为主,特征是不受特定空间、时间的限制,超越现实,以理想山水意象为依归,实际上写实的名胜实景图到了明代后期发展起来。

如黄宸的《曲水流觞图》以墨笔勾勒雅致精美的庭园,四周环境是一派清雅,描绘的人物场景是热闹喧嚣的世俗宴饮,体现的是雅俗兼备,既能体现风雅,又能满足鉴赏者和市民的文化需求。
再从许光祚的《兰亭图并书序卷》来看,非文人趣味在画中表现的更加明显,既有诗文唱酬,也有劝酒阔论的场景,童子侍从恭敬立于一旁,人物衣服颜色艳丽,花树繁茂,一派热闹的世俗。
既有文士的清雅,也有社交的俗腻。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的人物山水在对先辈艺术实践的继承中所流露出的文化和情感内涵,关注的是大众审美趣味融入艺术生活中。

任何关于雅、俗的价值判断容易陷入喋喋不休的争辩中,争论的偏激与片面性往往背离了对画家的基本认识或判断,这种情况就需要尽量避免。
在市民经济和精英文人风尚的影响下,人物山水画除了寄托山林情思,更要包含大众审美趣味。
因此明代中后期的文人画家出现了雅俗焦虑,在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的影响下,很难免于俗文化的包抄裹挟。

文人士大夫受到商业化浪潮的影响,可以凭借自身才识声望过一种相对富足安逸的生活,为了区别于一般的暴发户,标榜自身身份的清雅。
因此就出现了清供、清玩、清赏等生活方式,用美学小品书籍划分日常生活的雅俗界线。其实就是将日常生活艺术化,营造一种雅致古朴的生活氛围,包含了庭院草木、房屋桥梁、文房器物、膳食酒茶等细节事物。
如陈继儒的《小窗幽记》中写到,文人的乐趣就是种花调香,莳花弄草。明代文人开始追求现世生活的质量和享受,并从中发现了艺术趣味,带有文人独特审美的眼光,让生活更加精致化。

到了明代中期后,这种细致讲究更加深刻,在物质享乐的同时追求精神境界的愉悦,打造一种闲适优雅、遣兴移性的艺术化生活方式,将世俗和雅致融合。
世俗生活与雅致生活的并存,当时文人交往,认为谈论仕途经济是生活的庸俗化,认为诗酒棋花是生活的雅致化,可见两者是并存的。
一方面,文人受到商业化思潮的影响,可以凭借自己的经济地位,过着一种精致奢侈的世俗生活;另一方面,文人是社会精英的代表,可以避俗,进而追求一种雅致生活。

《长物志》中对文人书斋雅趣的生活各方面都有详细解说。
(2)仕宦与隐逸
隐逸一直是传统文化里讨论的命题,儒家和道家对于隐逸都有自己的看法,孔子认为,天下治理有道,就可以出仕,无道就隐逸不出,庄子认为,真正的隐士并不是身居山野不见世人、不发表言论,也不关心时事,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儒道认为隐逸的认知来源于个体的自觉和精神觉醒,梁漱溟认为古代的隐士在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都是处于一种自然淡泊的状态,隐逸超越了物质状态,上升到文人精神层面,是一种发自内心自觉的独立思想体现,为失意文人提供心灵的蔽所。

明代的政治生态很严峻,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处境比较艰难,因此仕隐的话题成了当时文人心中纠结的人生抉择。隐逸的理由有很多种,并一定都是因为仕途不顺而选择隐逸,范晔就做出了详细的解释。
这时白居易的“中隐”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不杜绝出仕的可能性,同时专注于文人生活情趣,在野就正心修身,寻求自身的意义,在出仕和隐逸之间寻找平衡点。城市山林就是这样一个折中的所在。
在仕隐观念上,宋元文人的遁世隐居是彻底的出世和与世隔绝,同样是追求隐逸,明人则将园林与山林结合起来,即城市山林,在喧闹的现实空间中构建一处远离世俗纷杂的清静居住地,沈周在《市隐》一诗中对于城市隐居有自己的见解。

这样的隐逸是建立在调节生活附庸风雅的情趣基础上,在日常雅化的事情上排解苦闷,寻求寄托。
明代很多文人都徘徊在这个抉择当中,与政治纠葛的牵绊常常让致仕文人对山水自然表现得更加青睐。
啸傲山林的高士,不论是身处庙堂,或是处江湖之远,潇洒高逸都是最高的精神境界,隐居乐道,林泉丘壑自古以来就是历代文人的追求,在仕隐观念上,明代很多文人无不徘徊于仕与隐之间,文徵明就是典型的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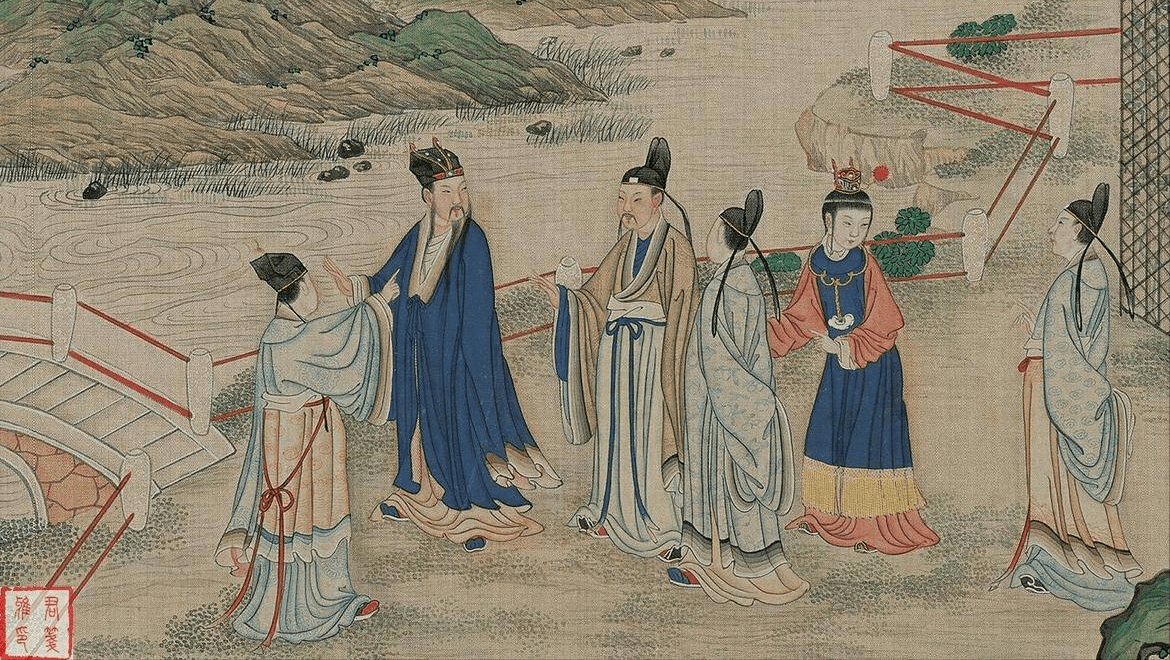
文徵明的思想包含着矛盾,他一方面真诚服膺儒学,做个坚定正统的儒者,努力按儒学的目标要求自己,心怀济世之志,却屡试不中,无从表见于世,成就功名,这是他从青年到中年遇到的最大挫折。
另一方面,他提出“人所自贵者,孰愈于仁?”,追求实现儒家“仁”的境界,“仁”与“乐山”、“静”有关,论语里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为了从矛盾中解脱出来,需要静心凝气感受自然山水之美。
文徵明意识到明代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入仕为官并不能达到“兼济天下”的理想,所以他选择了归隐故里。

文徵明在北京任官期间赋诗感叹不该抛弃平静的生活闯入北京官场,他从官场上全身而退,但精神还是要有所寄托,这一点在他1535年所作的兰亭图有所体现,草亭中的文士在深林掩映中,独立于画面下方的诗酒宴饮之外,仿王蒙层峦叠嶂的构图,山势婉转扭曲,S形上升的动势,幽深的山体与隐逸的主题正好相符,正是闲居适志,欣赏山水林泉的心境。
文徵明所倡导的失意文人清逸深秀的避居山水是明中期时的主流,当时因科举或官场失利的失意文士除文徵明外,有一批吴中名流如王宠、蔡羽、何良俊等,同样的感触和经历使得避居山水更能为他们共同接受欣赏。
山居隐士将文化传承作为山居生活的主要内容,儒家提倡“立德”、“立功”、“立言”,选择隐逸山林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尤其是政治失意挫败,“立功”的理想抱负被现实粉碎后不得不归隐山林,“立言”便成为隐士实现对社稷苍生的责任,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方式。

虽然离开政治舞台,但位卑未敢忘忧国,抛弃了尘世的功名利禄,生活和心灵趋向内向安静,得以潜心研究文艺创作。
明代中后期经济的成熟发展,使得民俗殷富的经济条件强化了文人对政权的疏离,他们不求闻达,归隐乡间,开池馆,艺松菊,戏弄翰墨,吟咏于猿鹤之间,怡然自得。
仕途不得志的文人画家将目光投向山野,隐逸生活的场所和日常成了画家作品主要表现的内容,“人”和“地”在画作中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隐逸之风的兴起进一步拉近了文人雅士之间的距离和关系,一起从时代的劫难中建立了相知共勉的友情,由文人或民间赞助者兴起的雅集活动就变得普遍常见,成为了取景入画的绝佳素材。
免责声明:本文为转载,非本网原创内容,不代表本网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